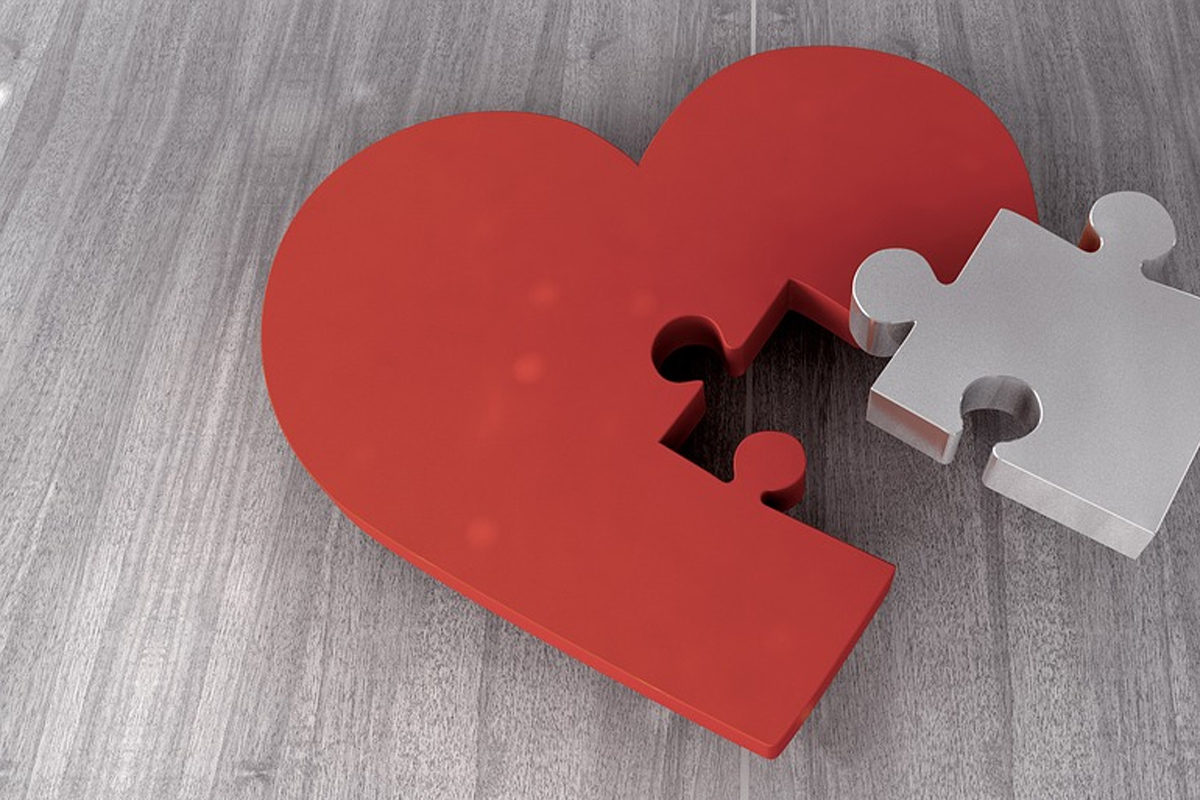
三千日子雲和月
很多認識我們的人都說,他們實在沒法想像:當初五、六個人擠在一間小房間的我們,居然能一路披荊斬棘的堅持到現在快百人的團隊。說實在的,沒有天主的恩佑、沒有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的慷慨捐贈、沒有加爾默羅隱修院修女們每天不斷的祈禱、沒有馮家姊妹一路的堅定相挺、沒有一路默默支持我們的恩人們,我們絕走不到今天。
尤其是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當我們願意放下我們原有的工作投入這塊園地時,修女們給我們的不只是一個閒置的教育基金會,還把院裡的一間神父休息室撥給我們當作辦公室。當成員逐漸增加時,修女們還把隔牆後的一間幼兒教室打通,讓我們每位員工得以有自己的辦公桌。後來是因為服務個案太多,為顧及學校和幼兒園的安全,不得不忍痛離開陪伴了我們四年的小窩,搬到唯一願意租給我們的美河市。
美河市雖然租金高,但一拐彎就上高速公路,為我們每天要到不同監所上課及外訪,實在方便太多了;加上打報告時有河畔夕陽的相伴,讓我們足足享受了將近十個月的幸福時光,但最後還是因為人員的不斷增加和龐大的租金壓力,不得不搬到木柵路的現址。但這次的搬遷,讓我第一次嚐到眾叛親離的滋味,壓力大到連我自己都懷疑這樣的決定對嗎?
還好,這棟屋齡超過40年老舊房子的房東並不是真的想自個兒使用,為舒緩年年不斷換會址的窘境,我乾脆心一橫,和房東簽下十年的租約,並向恩人以分期償還的方式借了一筆修繕費,把整棟已不堪使用的屋子整修了一番,樓上當辦公室,樓下作為實習餐廳,就這樣勇敢地開啟了我們社會企業的新頁張。
半年後(104年)的6月我們的七品聚實習餐廳開幕,隔年(105年)的6月,我們在鄰近處又租下了兩層樓建築物,一樓當人文咖啡小棧,二樓當諮商中心;再隔年(106年)的6月,緊鄰咖啡小棧的九個菓子銷售工作坊也跟著成立;再加上現在的六個外展單位:一家緊急短期安置機構-「選擇家園」、兩間少年團體家屋-「曙光家園」、兩個家庭服務中心(安康及大安文山)、一個剛新成立的桃園分會、一個臨時靠行的永安長青小站。每一塊拼圖,都記錄著三千個日子我們所串起的神話故事。
傻瓜兵團的召喚
二十年前,我們只是一群傻傻的教會志工團隊,抱著單純傳福音的理念到監所辦生命成長活動;哪知三天的活動才進行一半,全身上下甚至脖子上也都刺龍刺鳳的大哥們竟哭得像個孩子似的。之後的十年,我幾乎把所有的年休都給了監獄,直到有一天,當時在桃女監擔任主秘的淑華突然邀我們四個志工老師到她的辦公室,語重心長地說:「妳們光只在監裡面辦活動,這哪有難!妳們應該知道她們最需要的是出獄後怎麼幫她們重新站起來!」
當下的那一棒,雖然狠狠的敲醒了我,但回神後想到我的兩個孩子還小,我又有這麼重的房貸,我哪有能耐做甚麼?但說也奇怪,那次鴻門宴後的每個清晨彌撒,總有一個聲音催迫著我:「放下一切,跟隨我!」我越想逃,我的身體就越差,ㄍ一ㄥ到最後,失溫送進了醫院,我才不得不投降。接著,我的另一半、我們的幾個監獄牧靈志工…,一個個都被天主用不同的方式召喚在一起,就這樣義無反顧的倉促成軍。
開始的我們,為了能爭取到監所上課的機會,監所要我們怎麼做,我們一定全力配合;為了完成找家的夢想,我們甚至自掏腰包到香港參訪他們的戒毒工作,尤其是他們的中途之家;為了能拿到公部門的補助,在應徵不到專業人員的情況下,我們親自捲起袖子進學校讀書、修學分、考證照…。這期間不知道經歷了多少的困難、挫折和打擊,但我們不曾輕言放棄;更有很多次,我們是在憂心發不出薪水的情況下,邊上課、邊流淚。
但是我發現,不管我們怎麼使力,我們仍然撼動不了那塊巨石;倒是在跟毒品搶靈魂的肉搏戰中,找到了我們的戰略方針:絕對不能只停留在毒品的「預防」工作上,我們更要勇敢的站在反毒的最前線-「撈(中毒的)人」、「堵(製毒、運毒、販毒的)人、再生(重新翻轉)人」。
碰撞與磨合後產生的火花–多元與專業的結合
但說實在的,大部分被我們撈上岸的人,幾乎都已被毒品傷得遍體麟傷,可想而知,修復工程也絕非僅靠單一的面向就能成就;所以中期的我們,即使財務再困窘,公部門的方案補助只限於社工員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奢侈的將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引進到我們的團隊。只是沒想到光光讓機構內部的「社工組」與「心理組」能對上話,就整整磨合了三年;後來又加上跟助人領域沒有太大相關的「社企組」,同仁彼此間的適應與協調就更加的複雜,甚至耗盡了團體大半的精力。
所以,我們後來在徵聘新夥伴上,會把多元學經歷擺第一;因為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從不同角度被培育出來的專業人才,他的眼界和思維絕對會比只從單一學堂被培育出來的人更寬廣。這也造就目前機構同仁同時擁有社工、心理、企管、經濟、醫療、法律、行銷設計雙學位者,幾乎占了四分之一強。
為了鼓勵大家成為專業領域的尖兵,每周三的員工時間,我們會請學術界或業界的菁英,為我們上課;只要外部有專業講習或研討會,我們會盡量鼓勵同仁們參與;我們甚至會用加薪的方式,鼓勵同仁繼續進修相關系所或報考跟業務有關的專業證照。今年,我們就有三位同仁即將完成碩專班學程。這也讓我們目前員工在學經歷中擁有碩士學位或專業證照者,幾占機構同仁的三分之一強。
我們更鼓勵機構內的種子教師回學校或進空大進修,因為我們深信讀書能改變一個人的思維和自信心。目前十一個種子教師中,有九個都選擇繼續進修;其中,三個種子教師擁有社工師考試資格;鳴敏甚至在完成空專和空大社工學程後,繼續進修,這學期將要從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專班畢業;興國矢志要追隨鳴敏,今年也完成了社工學程。
至於我們的社企員工,我們也都配有不同的專輔老師,不斷地鼓勵他們考證照,幫他們規劃如何延續學程或請老師幫忙補習功課。我們的第一位培力少年就是在考上中餐丙級證照後,自動放棄三千元的加薪機會,而加入到我們的種子教師行列;之後,更在張祺老師的鼓勵下請家教補習功課,半年後,通過同等學歷考試,接著甄試上了大學的社工系。此壯舉影響了很多後進的培力員工,讓「讀書計畫」與「證照考試」成了陽光種子群組「戒菸叮嚀」外的另一個重要話題。
找錢,永遠是我們最大的夢魘
雖然,大家都說我們在協助藥癮者復歸社會上做得最徹底,成效也最好,但我們卻一直不受大眾捐款人的青睞,所以跟公部門申請方案補助就成了我們經費來源的主力。然而,政府方案很多都屬政策面或實驗型的,聰明又有財力的機構根本不會投案;只有我們,為了拼財源、養人才,只能壯大膽的去嘗試。然而,不管是標案或是委託案,在遴選過程中都會聘請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在一場場嚴峻的考核和挑戰中,雖然讓我們飽受不少折騰,但不同的時空交會,卻也厚植了我們的軟實力。
然而,方案接多了,除了自籌款、押標金和保證金也會跟著不斷增加外,一到年底,全辦公室得挑燈夜戰的趕期終報告、貼發票、趕核銷…。這還不打緊,我們還得面對來年方案是否通過的酸甜苦辣;更辛苦的是,方案的補助款除了常常緩不濟急、不能立即到位外,常常認真辛苦執行了一整年後,很多經費又囿於公部門的陳舊法規,只能看得到卻領不到;更有甚者,隔個一兩年,居然還會面對被追回去的夢魘。我只能說,接公部門案子越多,我們的心臟得要越強,口袋也得要越深。
尤其現在人多,每個月光勞、健保和勞退6趴,就將近55萬,相較於每個月不到一萬元的固定捐款,我們幾乎月月都在愁錢、找錢。我最記得有一年,對岸來了一個大善人,聽說帶著一捆捆的錢,要幫助有需要的公益團體;那年,我就好想攔住他,甚至連作夢都夢到寫信到對岸求救於他。
我也最怕碰到:「你們有多少錢,就做多少事;沒錢,就不要擴張這麼大…。」說實在的,我早就厭倦天天被錢追著跑的日子,但看著毒品犯罪不斷的飆升,新興毒品不斷的變裝,防不勝防的藥頭混入在我們的下一代身旁,以及成群結隊的為詐騙集團所利用的孩子們,我都會告訴自己:我們現在再不努力,我們的下一代怎麼辦?如果每個社福團體都因為募不到款而退場,我們的國家會變成什麼樣!
我們最大的財富是「人才」比「錢才」多
為了準備跟毒品打仗,我們除了不斷地籌措資金開拓場域外,有理念又優秀的人才注挹,更是我們站在前線屹立不搖的最佳武器。從八年前剛開始五、六個志同道合的夥伴,到現在成了將近百個老、中、青三代的組合。除了理念和熱情不變外,常常一場活動,我們的工作人員比參加者還多;為完成許許多多不可能的任務,各個幾乎十八般武藝都會。
也許就是風雨同舟的革命情感,讓我們每個員工的向心力都很強;面對強勁外武或疑難雜症,大家都會在第一時間不分彼此的捲起袖子。一例一休或每天的基本工時制,為一群在前線戰場上打仗的社福團體,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救人的工作是沒有時間表的,不能說停就停;尤其是我們所服務的高高風險個案,時間就是救命丹,看到同仁們為了夜訪或安頓個案,搞到人仰馬翻,我只能拼命祈求天主,讓我們多募到一點錢,能讓大家有個好年可過。
倡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與時間拔河
其實,要協助已經遭到身心靈全人破壞的藥癮者復歸社會,並非是件不可能的難事,它需要政府站在夠高的高度,去全盤考量;絕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撥些微薄經費,讓民間團體能做多少算多少,或視其彈盡糧絕後,紛紛退場;也不是找幾個專家學者紙上談兵,它需要的是無懼的堅持,站在最前線,分秒必爭的跟另一股勢力拔河。
如果藥癮者問題不能得到控制,社會上弒親虐童的新聞還是會不斷的增加。每次辦懇親會,想盡辦法苦勸家人來參加的同時,我們也心疼如果沒做好準備,家人再次受傷的扎心之痛,又有誰能體會;其實他們不是不願意改變,只是回家的這條路上荊棘遍佈,他們需要的是在不小心絆倒後,依然有人願意伸手拉他們一把。
我們常說,一個藥癮者要完全擺脫毒品的捆綁,期間會經過至少五~七次的復發;但試問,有誰能在他們又跌回去時即使伸出適當的支援?是司法單位?是地方社會?還是醫療單位?還是資源薄弱又無力的家庭?我們都知道新興毒品已經在校園及青少年族群氾濫,一般的預防宣導豈能跟得上包裝精美、魚目混珠的新興玩意,我們必須擁有足夠的胸襟和智慧,為退守做好準備,中介教育安置機構和類香港的群育學校就是最好的利器,否則,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我們的下一代,被毒品和犯罪集團所淹沒。

